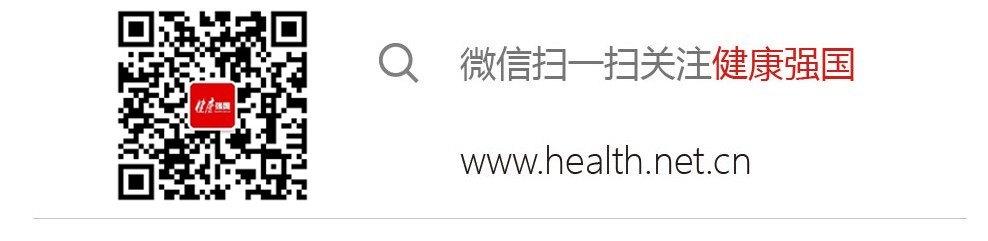标准治理的基本逻辑研究[0]
王平,侯俊军,梁正《标准科学》2019(11):27-34
摘要
治理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兴起,在国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国的标准化界和学术界也都普遍认为,标准在现代治理理论和实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本文结合治理和标准的概念,通过标准的产生过程和标准的实施传播过程梳理标准治理的基本逻辑。作者从标准化治理的视角出发,对国内外的对标准化的研究进行调研和梳理,对标准的产生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进行剖析,重点分析标准在标准化组织中的产生过程,企业内部实施标准的决策过程,标准在产业中的传播过程,以及标准中必要专利(SEP)对标准治理过程的影响,通过作者的论证和逻辑判断,归纳提炼出标准治理的基本逻辑脉络。、
关键字:治理、标准、标准化组织、标准联盟、RAND政策、标准中的必要专利
The Study on the Basic Logic of standards Governance
Abstract:
The theory of governance has arisen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and has produced extensive influence in China. China's standardization community and academia also generally believe that standards in modern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and standards, sorts out the basic logic of standard governanc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tandard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standard implemen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ndardization governance,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standardization, analyzes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s in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and the role they play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and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enterprises, the standards dissemination process in industry, also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 on the standards governance processes, and through the author's argument and logic, inducts the basic logic of the standard governance.
Key Words: governance, standards,SDOs, standards consortia, RAND Policy, SEP
1、概述
治理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兴起以来,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需要经济和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恰好形成现代治理理论能够适用的社会条件。我国的标准化界和学术界也都普遍认为,标准在现代治理理论和实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标准化的探讨还都集中在对标准的经济效益,以及标准与创新、专利、垄断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对标准和现代治理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标准化治理的视角出发,结合标准的基本概念和定义,对标准的产生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进行剖析,标识不同过程中的治理主体,研究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和其他影响治理的主要因素,对国内外的对标准化的研究进行调研和梳理,并通过作者的论证和逻辑判断,归纳提炼出标准治理的基本逻辑脉络。
2、治理的基本概念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把治理(governance)定义为:治理是各种人和机构(包括政府的和民间的)处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并达到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正式机构的和体制授权的强制性服从过程,也包括人或机构都同意的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1]
Jessop B(1998)指出,一般来说,可以识别出(治理的)两种关系紧密且互相嵌入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互相依赖的活动之间任何类型的协调,其中包括三种类型,无序的交换、组织的层级结构(hierarchy[2])、以及自组织的平序网络结构(heterarchy[3]);第二种含义更狭窄,仅指平序网络结构(heterarchy)或自组织……,其形式包括自组织的人际网,经谈判的组织之间的协调,以及去中心化的,受环境调节的系统间调控。后面两种情况涉及到多代理、多机构和多系统的自组织调控,彼此之间独立运作,但是因为相互依存而在结构上又相互联系。这两个特征对促进依赖于平序网络结构(的治理形式)尤为重要。[4]
郁建兴和刘大志(2003)指出,治理理论明确提出了多中心治理观点,使得一直由行政官僚负责的具体公共事务这部分自留地,也不得不向个人和其他组织开放,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来共同管理,从而分享国家对内主权中的行政管理权部分。申建林和姚晓强(2015)归纳出治理的基本理念和规范: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二是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三是主体间权力的依赖性,四是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一种管理形式只有具备了这四种要素,才能称之为“治理”。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行为相比,治理具有更多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性的特征,如去中心化、去确定性、去结构化等。
所以,治理问题研究主要是针对相对独立的实体(组织或人)之间的互动和协调关系,既包括民间自组织的过程,也包括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互相独立的治理主体又互相依赖,通过互动、协调和同合作,共同发挥作用推动共同事业的发展。结合治理的基本概念,我们可以认为,标准治理的基本逻辑研究首先要标识出治理主体,研究治理主体在标准的产生、实施、传播过程中的行为,对治理过程的贡献,治理主体参与标准化的诱因和主观意愿,它们受到的外部环境的压力,影响治理的其他要素等,然后梳理出标准治理的基本逻辑脉络。
3、标准治理的基本逻辑
3.1 标准的产生过程
3.1.1传统标准化组织
一般情况下,传统标准化组织本身并不对标准内容采用的技术方案施加任何影响,完全由利益相关方自己做出决定。标准化组织的基本责任是提供确保标准制定过程“公开,透明,协商一致”的游戏规则,防止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受到侵害。利益相关方派出的专家在标准化组织中扮演谈判代表的角色,各自都有相应的利益诉求和激励诱因,在标准组织中交换知识资源,披露知识产权,讨论技术方案,可能要经过激烈的争论、讨价还价和妥协,通过既定的游戏规则(如协商一致)找到统一的技术解决方案,利益相关方最终达成技术协议,从而标准化组织能够产出标准。标准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是平序(heterarchy)网络结构的一种。他们各自独立运作,各种标准化组织成为他们在技术上互相联系和协调的网络节点。
标准化组织也为参与标准化的个人形成人际网搭建了平台。例如, Murphy C & J Yates(2009: 36-42)指出,当人们加入到标准化委员会当中,进入了一种“协商民主”的环境,……把这些工程师们带入了更大的社会网络,让他们还扩展了布迪厄认为的资本形式——即增加了“社会资本”(Bourdieu P. and Wacquant L.,1992)[5]。Brunsson(2012)认为,代表公司或利益集团参加标准化组织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代表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
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标准化组织在全球不同的国家中最终形成的管理体制是不完全相同的,特别是国家级标准化组织(NSO[6])。美国的ANSI[7]就是纯粹民间组织;欧洲国家的NSO虽然也都是民间组织,但是它们普遍都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协调关系,带有一定的政府色彩;很多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NSO都是完全由政府负责管理的模式。虽然这些NSO的高层管理模式不同,但是在主导制定标准的技术组织模式是基本相同的,大都采用传统标准化组织的委员会协商一致的形式。这就形成了在管理体制不相同情况下,标准化活动的基本治理逻辑与前面所讨论的是大致相同的。当然,政府管理模式可能会造成有些重大标准的制定过程可能会受到政府干预,致使标准治理路径的偏移。
3.1.2 标准联盟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标准化组织繁琐的“协商一致”大大限制了其跟随技术发展的步伐。因此,Brunsson(2012)所谓的标准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广泛性和制定标准的效率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变化。对于标准组织的合法性(legitimacy)来说,制定标准的效率比起参与的广泛性和协商一致规则显得更为重要了。这大大促进了标准联盟的发展。
联盟组织有的更加开放,有的更加封闭;有的联盟成立新的法人实体,有的则仅仅采用签署合作协议的形式;有的联盟对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进行限制,或者不采用会员制;制定标准的形式也更加灵活;标准的制定周期大大缩短,效率也大大提高。例如,IETF是典型的民间标准联盟组织,属于比传统标准化组织更加开放的一类。它不设组织会员,参加人都只代表个人,也不收会费。制定标准的过程真正成为专家之间的技术协调,而不是公司利益的代表之间的追逐私利之争。IETF认为,投票方法可能会造成少数人正确的观点被压制。所以它用Humming[8]方法代替投票,称为“大致的协商一致”。还有一个相对开放且非常成功的标准联盟案例是W3C[9]。 W3C是通过协议形成的联合体,不是法人实体。它有4个签署了合作协议的全球总部(W3C Hosts)负责全球团队联合运营。W3C的收入主要来自会员费、政府及企业的研究经费、赞助与捐赠等。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采用签署协议的形式成为其会员。W3C对企业收取的会费是按照企业规模来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企业大小加入W3C都不会有太大压力。所以它相对来说是很开放的联盟。
另外一类联盟组织采用更加封闭的组织模式。例如3GPP[10],它也不是一个法人实体,而是由7个国家或地区的电信标准化组织[11]签署协议发起成立的联合体。3GPP的会员分为三类:标准化伙伴组织、市场代表伙伴组织和个体会员。3GPP制定标准的过程依然可以认为是协调过程,主要是企业利益的协调,达成的结果是企业技术方案之间的妥协。其封闭性让它成为了少数公司谋取私利的场所。它收取的会费很高,致使少数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垄断了它的标准。封闭型的标准联盟在现实中很普遍,它已经成为企业合作制定标准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
尽管标准联盟的组织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从治理角度对标准联盟组织进行分析的关键要素还是类似的。它依然是人与人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进行互动和协调的场所。以专家为主的联盟则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专家之间的协调,组织利益被弱化。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开放的联盟之中既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也有专家人际网的协调。相对封闭型的联盟主要表现为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专家知识被弱化,组织(如企业)之间的利益协调被强化。参与联盟的企业、研究机构等利益相关方以及作为个人参加的专家以联盟组织为平台,形成互相联系的平序网络(heterarchy)。
3.1.3 技术法规
技术法规的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安全、人身安全、环境保护等内容。各个国家的政府制定技术法规采用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我国的强制性标准的产生与自愿性标准的产生源自同一个标准化体系。而美国的法律要求政府技术法规应该主要引用民间的自愿性标准。当欧盟政府由于市场监管需要某一种技术法规的时候,其做法是向欧洲三大标准组织进行咨询。则欧盟政府的技术法规或者直接引用已有的自愿性标准,或者向标准化组织发出制定一项欧洲标准的委托书(mandate),然后引用。
必须明确的是,政府官员并不是技术专家,他们无法自己单独制定技术法规。他们如果引用了民间的自愿性标准,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资源,而且能够体现民间自愿性标准能够及时解决产业问题的优越性。如果政府自己制定强制性标准,它也无法完全靠自身的权威性来完成,也必须向来自各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所以,技术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制定过程依然是多主体的互动过程。
3.2 标准的实施与传播
3.2.1 实施意愿与外部压力
在工业当中标准治理的主体全部是实施和传播标准的企业。虽然治理的概念强调不同独立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协调过程,但是单个企业实施标准是企业之间出现标准协调的起点。企业采用自愿性标准首先需要企业自身的意愿。经济学研究一般认为传统企业采用技术类标准的诱因为了提高效率并形成规模化生产,以及在ICT领域企业采用互操作性标准是为了市场竞争,或者作为一种战略选项。这是由于互操作性标准常常和正的网络外部性直接相关 (Katz & Shapiro, 1986)。Brunsson等人(2012)的组织研究认为组织采用标准,第一,为了应对来自外部制度环境的压力,其二是为了提高组织自身的效率,其三是为了提高组织的运行业绩。
一个企业主动采用的技术类标准非常之多。例如一个设计人员在考虑创新技术的同时还会面对成百上千的技术标准。这些技术标准绝大部分经过长期的工业应用已经非常成熟,采用这种技术标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具有强意义上的合法性(王平、侯俊军、梁正, 2018)。另一方面,当一个企业的产品设计面临新出现的技术标准的时候,它需要经过慎重的决策过程,包括考虑采用新技术标准可能需要技术变更和资源投入,淘汰原有技术,还可能要作废掉原有的部分投入等。创新技术标准的实施属于弱意义上的合法性(王平、侯俊军、梁正, 2018)。
除了自身的意愿之外,企业是否执行标准也受到的外部的压力。例如,Brunsson(2012)指出的制度理论在传统上强调标准的采用和传播与受到的压力有关,如受到强制(coercive)、规范化(normative)以及模仿同构(mimetic isomorphic)的压力作用(DiMaggio & Powell, 1983)。外部压力可能来自于政府的技术法规或强制性标准,也可能来自民间组织(第三方认证和测试机构),或来价值链中的自他企业。外部压力不仅促使标准在企业的应用,也是造成标准在企业之间传播的重要原因。
3.2.2 标准传播及对市场的组织
标准在市场中(企业之间)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产业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统。如果一个在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企业(可能是参与制定标准的企业)开始实施某项新的技术标准,它会利用自己在工业生态网络的优势位置要求相应的上下游企业也开始采用该标准。生态网络中的核心企业和周边的上下游企业虽然都是独立运作的,但是会形成某种形式的技术协调关系,并且还可能伴随着专利的授权。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上下游企业往往会受到核心企业的压力而采用标准,否则可能会有被核心企业从价值链中剔除的危险。这种企业之间的技术协调关系和商务关系让标准承载的技术方案迅速传播。标准的传播与实施是技术规则在工业过程、经济发展或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过程。创新技术形成的解决方案最终能够形成规模效应,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标准治理最终产生效用的过程。
经济学家认为,标准能够降低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Akerlof, 1978),能够帮助企业降低客户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刺激重复购买行为,扩张总体市场规模(Büthe & Mattli, 2010)。而Brunsson等人的组织研究则认为这都是标准组织市场的重要方式。标准通过提高系统组件的兼容性和协调性,促进市场的组织,让各种市场参与者(例如竞争对手)的利益保持一致,并加强了沟通。标准有助于制度的变迁,还能够缓解模仿同构的压力。模仿者不需要探究现有或正在形成的制度和秩序的细节,而只是按照标准的要求行事。(Espeland & Stevens, 1998)。
3.3 标准与知识产权
3.3.1 知识产权政策
随着ICT产业的发展专利问题成了标准化组织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ITU、欧洲标准化组织CEN/CENLELEC/ETSI、以及各个国家的标准化组织,以及很多民间标准化协会(ASTM、IEEE等)和各种联盟等都陆续发布了各自的知识产权政策。
下面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ITU的知识产权政策[12]为例进行说明。ISO/IEC/ITU的专利政策首先要求标准制定的任何参与方应该向ISO/IEC/ITU提供有关专利(自己的或其他机构的)及其所属的机构的信息,即所谓的专利披露。在披露专利之后,专利持有人对其专利权可能持有三种不同的意愿。第一种是他同意以RAND原则[13]与其他各方协商,提供专利的免费许可。第二种是他同意在符合RAND原则的基础上向其他各方收取专利许可费;第三种是他收取专利费但不以RAND原则为基础。ISO/IEC/ITU在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下都同意专利可以纳入到标准之中,而对于第三种情况则不同意。ISO/IEC/ITU的专利政策并不负责由此产生的许可、专利费等必要事项等,而是留给由具体的参与方自己决定。ISO/IEC/ITU对于这些专利也不负责提供有关证明、有效性和范围等权威信息。几乎所有的传统标准化组织都采用了与上述国际标准化组织相类似的专利政策。还有一个词FRAND[14],与RAND的含义相同,两个词可以互换。
3.3.2 RAND模糊性与法律规制
标准化组织采纳RAND原则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会员通过把知识产权纳入到技术标准中而滥用知识产权许可。另一方面,RAND承诺也确保专利持有人能够从标准的用户收取到合理的专利费,从而补偿技术投入对标准做出的贡献。然而事实说明,仅仅是标准化组织的RAND政策无法对企业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标准具有的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使得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获益空间大大延伸 (孟雁北,2014)。专利持有人有可能通过过度披露的办法为将来谋求多收取专利费,打官司谋求更多的赔偿。这造成专利持有人可能把标准的必要专利和其他很多不必要的专利都一起拿出来披露,形成专利丛林(patent thicket)。此外,多披露还可能掩盖不披露,而不披露专利或者恶意的隐瞒专利(专利埋伏)又成为企业与对手的一种竞争策略。
由于专利持有人一般都是实力强大的跨国企业。大部分标准用户一般情况下与这些专利持有人相比处于弱势。特别是中小企业,他们没有和专利持有人平等的谈判地位。RAND原则非常模糊,几乎没有标准化组织对公平合理无歧视做出定义或清晰的阐述(Lemley, 2002)。只要技术标准所包含的技术方案落入专利的保护范围, 则该专利的权利人就拥有劫持整个技术标准得到实施的巨大控制力(张平等,2008)。专利权的存在可能导致对标准制度的“劫持”(Hold Up)和专利许可费堆积(Royalty Sacking)等问题(Lemley,2007)。
另一方面,标准的用户(运营商或手机制造商)中也可能产生实力较为强大的企业。这种企业有实力与专利权人进行抗衡,甚至出现专利反劫持(patent holdout)的案例。过去产业界、司法界和学术界更多关注标准必要专利中的专利劫持问题,对反向劫持问题研究较少(王瀚,2018)。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负责人Makan Delrahim 2017 年11 月的一次演讲中宣布,美国司法部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执法重点,将从聚焦专利劫持向反向劫持转变[15]。
标准对技术的锁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可能让标准形成很大市场支配力。而企业的本质是追逐利益最大化,RAND的模糊性又很难约束专利持有人和被许可人的行为。目前出现大量与SEP有关的案例都说明了最终还只能由法院和政府的法律规制来主持正义。只有当专利持有人的垄断行为和被许可人的反劫持行为落入法律规制的时候,才有可能恢复扭曲的市场竞争。
3.3.3 SEP与创新
对SEP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标准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可能促进技术变革和技术的扩散,但也有可能阻碍创新(Blind K, 2013);SEP对于连续性的技术进步有着很强的正向影响,但是它对非连续性的标准替代有着显著的延迟作用(Baron J, Pohlmann T & Blind K, 2016)。最基本的逻辑是,如果企业技术标准与企业的创新方向一致,则技术标准肯定促进创新,反过来则阻碍创新。
Busch L (2011:91,92)的研究指出,当欧洲早期的无线通信领域只有一个统一的GSM标准的时候,美国的完全自由竞争理念则允许两家公司T-Mobile和Deutsche Telekom用不同的技术标准进行竞争,结果让美国在无线通信领域的竞争力远远不如欧洲。美国的标准割据实际上让客户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无所适从。欧洲的统一标准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竞争平台,大大促进了运营商和手机制造商在标准平台上的创新。后来进入了4G时代,3G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4G创新,因为创新技术还要兼容老的标准,运营商希望还要留住继续使用3G的老客户,这就要大大增加了创新成本。SEP对于全球标准化体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持有标准中核心技术专利的专利权人具有做出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在可能性,运用“战略性专利申请”与“事实工业标准”相结合进行寻租已经改变了国际标准化体系运行的动力(Ernst D,2012)。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由于专利进入到标准之中,增加了标准治理过程的复杂性。标准组织不再仅仅是协调利益相关方的场所,也成为一些企业试图把自己的技术创新与标准的市场影响力相结合的场所。企业把自己的专有技术制定为标准能够提高其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标准的特性因此从公共品向私有化偏移。由于网络技术的外部性,在实际当中ICT产业中的核心技术标准总是把持在少数实力强大的跨国企业手中。进入到标准中的专利可能成百上千。然而,这种向“私有化”偏移的技术标准(如4G、5G标准)所支持的通信网络最终还会成为被全球广大客户所接受的重要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4. 结论
标准治理包括标准的产生、实施和传播过程中组织或人之间进行的协调过程。当今的标准治理主要体现为标准化组织中或产业中的自治理过程,形成了现代标准治理的特色。本文论证无论是标准化组织形成的治理网络还是产业生态系统形成的治理网络,它们都属于自组织的平序网络结构(heterarchy)。网络中的实体(组织或人)之间都是独立的,但是都处于某种互动和协调关系。自愿性标准的产生过程既包括完全民间自治理的标准化,也包括政府作为管理者的标准化;既包括传统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化,还包括ICT产业中的各种联盟组织的标准化。这一过程表现为以标准化组织为节点聚集互相独立的利益相关方,所形成的治理网络是多样化的星形平序网络结构。传统标准化组织往往是组织(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治理网络和专家人际网的叠加,而不同的标准联盟组织随着参与方的不同所形成的治理网络可能是专家人际网,也可能是多种利益相关方形成的网络,还可能仅仅是若干企业形成的治理网络。
标准的实施和传播过程依赖于产业价值链和生态网络中的各类企业之间存在的技术协调关系和资源配置关系进行传播。产业生态网络成为标准传播的重要治理网络。其中的核心企业和周边的上下游企业都是独立运作的,但是在标准的传播过程中形成某种形式的商务和技术协调关系,还可能伴随着资源的传递(如技术知识的传递、专利许可等)。这种生态网络也是一共平序网络,各自独立的企业形成一种自治理形式的利益共同体,让自愿性标准承载的技术的迅速传播。标准的实施与传播是技术规则在工业过程、经济发展或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过程。创新技术形成的解决方案最终能够形成规模效应,推动经济的发展。标准中的必要专利(SEP)实际上是两种知识载体的叠加,已经深深地影响标准治理过程。标准化组织中的RAND政策提供了一种基于诚信的知识产权披露规则,但是对企业的规制效果有限,最终还需要反垄断法的力量进行规制。政府作为标准治理主体之一主要体现在技术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技术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制定过程依然是多主体的互动过程。
作者简介:
1、王平,研究员,原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资深顾问研究员。重点研究方向为标准化历史和基本原理、标准化与创新、企业标准化以及国际标准化等;共发表中英文论文50余篇。
2、侯俊军,博士,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标准化与治理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专著3部。
3、梁正,经济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标准与知识产权、研发全球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与实践;发表中英文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和参编著作10部;主持或参加包括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在内的多项国家级重大咨询课题和国家级科研项目十余项。
参考文献
[1] 鲍勃·杰索普,漆蕪. 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01):31-48.
[2] 郭毅, 可星等. 管理学的批判力[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46-82.
[3]孟雁北.标准制定与实施中FRAND承诺问题研究[J].电子知识产权,2014(11):26-30.
[4]申建林,姚晓强. 对治理理论的三种误读[J]. 湖北社会科学,2015,(02):37-42.
[5]王瀚.美国标准必要专利中反向劫持问题研究[J].学术界,2018(03):189-199+279-280.
[6] 王平. ISO全球标准化网络中的自愿性与协商一致——墨菲与耶茨对ISO标准化与全球化的探讨[J]. 中国标准化,2015,(08):53-60+66.
[7] 王平,梁正.我国非营利标准化组织发展现状——基于组织特征的案例研究[J].中国标准化,2016(14):100-110
[8] 王平,侯俊军,梁正.治理视角下的标准知识体系研究——标准治理逻辑和学术研究现状综述[C]//侯俊军主编. 标准化与治理(第二辑) [M].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
[9] 郁建兴,刘大志. 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2):6-14.
[10]张平, 张小林, 何怀文.技术标准化中知识产权披露机制研究——以3G产业为背景[J].网络法律评论,2008,9(00):3-20.
[11] Akerlof G A.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M]//Uncertainty in Economics. 1978: 235-251.
[12] Baron J, Pohlmann T, Blind K. Essential patents and standard dynamics[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9): 1762-1773.
[13] Blind, K. The Impact of Standardization and Standards on Innovation [J]. Manchester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Research, Nesta Working Paper 13/15, November 2013. http://www.innovation-policy.org.uk/share/14_The%20Impact%20of%20Standardization%20and%20Standards%20on%20Innovation.pdf
[14] Bourdieu P, Wacquant L.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19.
[15] Brunsson N, Rasche A, Seidl D. The dynamics of standardization: Three perspectives on standards in organization studie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12, 33(5-6): 613-632.
[16] Busch L. Standards: Recipes for reality[M]. Mit Press, 2011.
[17] Büthe T, Mattli W.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Standard‐Setting Bodies[M]//The Oxford handbook of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2010.
[18] DiMaggio P,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an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 147-160.
[19] Espeland W N, Stevens M L. Commensur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1): 313-343
[20] Ernst D. America's Voluntary Standards System--A" Best Practice" Model for Innovation Policy? [M]. East-West Center, 2012: 20-31.
[21] Jessop B. The rise of governance and the risks of failure: the c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 50(155): 29-45.
[22] Katz M L, Shapiro C. Technology adoption in the presence of network external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4): 822-841
[23] Lemley M 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J]. Cal. L. Rev., 2002, 90: 1889.
[24] Lemley, M A. Ten things to do about patent holdup of standards (and one not to) [J].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2007,48:160-171
[25] Murphy C N & J Yates.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voluntary consensus[M]. Routledge, 2009.
[26] Nair A, Prajogo D. Internalisation of ISO 9000 standards: the antecedent role of functionalist and institutionalist drivers and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009, 47(16): 4545-4568.
[27] Stigzelius I, Mark-Herbert C. Tailoring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o suppliers: Managing SA8000 in Indian garment manufacturing[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25(1): 46-56.
[28] Tolbert P S, Zucker L G.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hange in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The diffusion of civil service reform, 1880-1935[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3: 22-39.
脚注(文中的标号都为脚注)
[0]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标准化对自主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及相关公共政策研究”(项目号7137313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与应对政策研究”(项目号7144102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标准治理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研究”(项目号17ZDA099)共同资助。
[1] 这段文字的原文见Our Global Neighborhood: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Chapter One, A New World. http://www.gdrc.org/u-gov/global-neighbourhood/
[2] 社会学把Hierarchy又译为“阶序”。
[3] 在社会学中 “平序”(heterarchy)与“阶序”(hierarchy)相对应。平序网络是一种平面的,没有上下层级关系的网络。
[4] 这段文字翻译部分参考了漆蕪的译文,见鲍勃·杰索普,漆蕪.(1999)。
[5] 这段翻译文字见:王平(2015)
[6] 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7]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8] Humming 在这里特指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工作组负责人与组员互动的一种方法。例如组长在必要的时候向全体组员询问对某一方案或几个方案持有的态度,组员的回答可能是Yes或者是No,从而决定下一步的讨论方向。这种对问题的应答称为Humming。但是Humming不能作为投票,它只是讨论问题的开始。详见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282
[9]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万维网联盟
[10] Thi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即3G合作伙伴项目。
[11] 这七个标准化组织包括:ATIS(美国)、ARIB(日本)、CCSA(中国)、TTC(日本)、ETSI(欧洲)、TTA (韩国)、TSDSI(印度)。
[12] ISO, IEC, ITU.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on Patent Policy for ITU-T/ITU-R/ISO/IEC,2016-06-26. 见http://www.iec.ch/members_experts/tools/patents/documents/ITU-T_ITU-R_ISO_IEC_Common_Guidelines_2015-06-26.pdf
[13] RAND: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翻译为合理无歧视,即意为:以合理的条件,在无歧视的基础上与各方协商的原则。
[14] FRAND是与RAND相类似的一个原则,即: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译为公平合理无歧视。
[15] Justice News.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Makan Delrahim Delivers Remarks at the USC Gould School of Law's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Conference, November 10, 2017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ssistant-attorney-general-makan-delrahim-delivers-remarks-usc-gould-school-laws-center
来源:王平,侯俊军,梁正王平的标准化文章